理工大牛人写的旧体诗词,把中文系教授看哭了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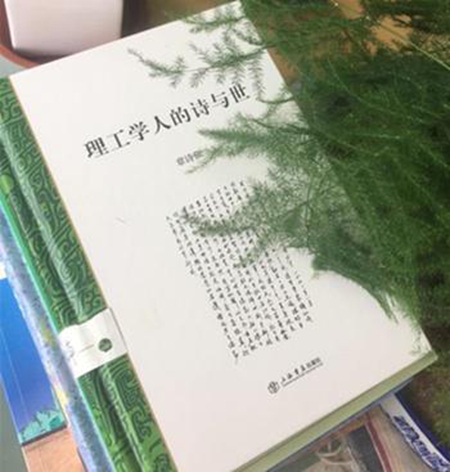
章诗依 《理工学人的诗与世》
2017年5月,章诗依的专栏结集《理工学人的诗与世》入选华文好书月度推荐。在各大媒体书评版,也陆续刊出了刀尔登、谢泳、袁凌等名家的专文推荐。有书评称曰:“会写旧体诗的科学家,以后不会有了。”“这些大牛写的旧体诗词,把中文系教授看哭了。”
是的,谁能想到,中国计算机先驱者可以写出“举国纷纭忙狗盗,权门交易尽民膏”这样的句子,而天文学家在牛棚里可以写出:“且喜诗书销海内,更收珍丽实关中。赢来一赋阿房宫”这样兼具咏史与写实的词意。而将这些散落的珍珠收拾成文,并详细介绍这些理工牛人另一面的书,是因何种因缘而问世呢?
1、一个典型媒体人的书架
两室一厅的房间里,除了厨卫之外,没有哪一面墙上没有书架。主人介绍说,这就是一个“典型的媒体人书架”,各种各样的书,非常杂。而我们的采访,就选在了一个排满了各种珍版书的书架前,听主人一一介绍自己的得意收藏。
“常看的一本书是张季鸾的,这是上海书店90年代初影印的一套书,是张季鸾去世大概过一两年,《大公报》同事给他出的纪念版社论集。我为什么常看这本书呢?因为他这个社论写得时间很久,跨越时间很长,基本上可以作为民国那一段、19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历史来阅读,至于他的社论写作技巧大家是公认的,也可以学习很多东西。”
章诗依,这个文艺的名字背后,藏着一个名字叫做“张修智”的知名时政新闻人,从上世纪末进入新华社,后来参与创办知名刊物《瞭望东方周刊》及《财经国家周刊》并任副总编辑。在他的藏书中,媒体类显然有着不同的地位。在推荐给网友的藏书中,除了张季鸾的社论集,还有1990年代新华出版社的《普利策新闻奖特稿》。“新闻文本写作的水准,我觉得现在还应该需要学习。”
当然,能够写出《理工学人的诗与世》这样的书,既需要对新闻资料的寻访搜集,也要有对传统文化,特别是旧体诗词方面的爱好与涉猎。所以,在介绍对自己影响比较大的书籍时,章诗依推荐了陈之藩的散文、潘光旦的《铁螺山房诗草》、法学家萧公权的《画梦词》,前者是理工学人的人文思考,后两者,则是学人的诗集。
“陈之藩先生是学机械的,但是他文章写得特别好,作为理工学人,他写的散文里面,会有很多人文学者看不到的学科交叉的思考。”
对于学人的诗集,章诗依经常一边看一边抄录,他说,这是“又练书法又读诗”。
“还有一本比较喜欢翻的,《徐燕谋诗草》。徐燕谋是复旦大学英文系的教授,但是他的古体诗写得很好,而且他也是和钱钟书先生唱和最多的一个人。这里面有钱钟书先生做的序,钱钟书轻易不给人做序的。”
2、诗,一个通往人内心深处的渠道
为什么会写《理工学人的诗与世》这样一本书,其实在书架上已经找到了一半的答案。但章诗依自己在阐述缘由的时候,却把时间线拉回了他的高中时期,一个文科生偶然买到一本书,讲一位物理学家和朋友们一起谈论文艺,谈论诗,一起欣赏音乐……但是,后来,他忘记了那本书的名字,也就断绝了在任何网站找到那本书的可能。
后来,又是一个偶然的时间,他读吴宓的日记,看到其中提到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给吴宓寄诗,但吴宓在日记中对胡的诗评价很低,这使他反而对胡诗产生了兴趣。“我看了还觉得不错,我可能没有那么高的要求。后来就看胡宗刚先生写的《不该遗忘的胡先骕》,从年谱里面发现了胡先骕他列举了一批科学家,那个名单大概有二三十人”。
胡先骕的传奇性和影响力,不仅仅在中国的科学界,在中国文化方面,也有着非同寻常的经历,可以说是学贯中西兼通文理。他参与过著名的新文化运动,但是却站在传统文化的立场批评白话文和文学革命,还与吴宓等联办过知名的《学衡》杂志。“突然发现有这样一个人,有那样一个过去,曾经那么一个非常活跃,甚至可以说是显赫的时期,他后来怎么样呢?他最后的命运怎么样?他在后来怎么想的?这让我很好奇,想去挖掘。”
于是,从胡先骕开始,一条线索,因为偶然的原因,延展开来。成就了这本《理工学人的诗与世》。他是中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奠基者,
只是,这本书,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多人诗歌集结,关于诗本身的描写,在全书中只占三成左右,更多的篇幅,是讲人,人的性情,人的生平际遇,并衬出那个巨变中的时代。
在章诗依看来,看那些理工学人的诗词,不只是一个纯粹文学性的欣赏,更是“进入那些学人内心世界的一个工具”。“诗是很个人的一个写作,如果你想了解他内心比较隐秘的一些东西,我觉得诗歌是一个非常好的渠道。有的时候他不可能写文章,但是他会通过诗歌表达自己。我实际上想通过诗歌来了解这些学人不太容易表达的东西。”
这种“不太容易表达的东西”,在《理工学人的诗与世》一书中有着很多故事。最典型的一例是,1944年,翁文灏次子在对日作战中牺牲殉国,他在五天后接受《大公报》采访的时候,报道称:“翁部长谈起殉职的儿子时,没有叹息,甚至谈笑时没有半点不自然……”但是,那种云淡风轻,只是表面。在《哭心翰抗战殒命》诗中,他对丧子之痛的描述,锥心泣血。在抗战胜利后的《追哭翰儿》四首中,仍有“秋风秋雨忆招魂,胜利反教流泪痕。南望一棺江岸畔,放牛坪上尚安存”之句。
3、故纸堆中的珍宝
在《理工学人的诗与世》中涉及的科学家们,其官方的生平介绍,往往更着重于他们在本行业内的成就贡献,但他们私下里的爱好,他们的诗词,还有一些比较私人的生平资料,其实很难在一些常见的文本中找到。即使是胡先骕先生,他跟胡适先生的合影,今天也被很多人误以为是陈独秀。大众会认错,其实说明大多数人对他是比较陌生的。
在章诗依看来,科学家的声名不显,并不难理解。“科学家一般情况下是寂寞的。只有在科学有重大发现,或者关系到民生重大的科学创举时,可能会出现明星科学家,比如像霍金,多数科学家平常都是默默无闻的。胡先骕当年那么活跃,包括毛泽东都知道说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,他的寂寞身后,也有一些时代的原因,也有一些个性的原因,比如他这个人比较书生气。”
好在,身为媒体人,章诗依对于在“故纸堆”中寻找有价值的内容,可以说轻车熟路。比如,对年谱的考证。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的一些事迹,正是来源于年谱。
“翁文灏先生有一个诗集,团结出版社出的。那个诗集里面最有价值的就是翁文灏怀人的作品,怀念他很多早年做研究还有在从政时代打交道的一些同事朋友。解放以后,他作为政协委员,还享受一些待遇,经常到各地考察,也有一些讴歌新时代的作品。但是他的儿子在书的后记中心有不甘地说,我父亲并不是只写过这些。果然,我后来在他的年谱中发现了更多东西。”
在《理工学人的诗与世》这本书中,涉及到22位科学家,胡先骕、石声汉、秉志、翁文灏、欧阳翥、黄万里、阚家蓂、丁文江、梁希、周太玄……其中,有人在大众层面非常著名,比如曾任政府公职的丁文江、翁文灏,但更多的理工学人,名字并不为大众所知,仅仅是在专业领域享有盛名。照章诗依的说法,“有个别通过搜索引擎都无法查到详细资料”。所以,在资料查找方面,自然也有着难易之别。
“我就简单先把他们写出来,如果更深入可能,再去深入。”
4、诗的时代过去了,但并不需要哀叹
在《理工学人的诗与世》这本书中所描述的科学家们,都是少年时打下了深厚的旧学功底,又有留学的经历,可以说是中西文化兼通的一代人。
“这些人的存在,证明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没有阻碍中国人接触现代科学。”
“在传统文化中,诗歌是我们最精髓的一部分,最中国的一部分。”读诗,特别是旧体诗,是章诗依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随身携带一本袖珍版的白居易诗集,或者把诗集作为礼品送给朋友,甚至在同学群里以诗互相赠答,已经成了一种日常。虽然,他谦虚地把自己的诗称作“打油诗”,无论如何不肯示人。
在被问到为什么会更喜欢旧体诗的时候,章诗依想了想,解释说,格律工整的旧体诗,有点像一个有趣的、挑战想像力的游戏。“这些诗句的安排,就像玩积木一样。组合排列,真的是千变万化。”
但是,时代变了,让现代人再去学习写古体诗,即使爱诗者如章诗依,也并不认为答案是肯定的。“那个时代已经不在了,这一代人也是机缘巧合,因为他们在从晚清过来,那个时候传统文化没有被激进摧毁,同时他们又有机会到西方接受新的科学学习和训练。你很难遇到这样一个历史机会。”
“假设说我们的教育系统体系真正认为诗歌是有价值的,而且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,如果想恢复(这种教育),我觉得是有途径和手段的。现在有一些学者他们是个人努力,不成气候。要编一套很好的教材,从四五年级开始有一个诗教,也不一定让他们有多高的水准或都能做诗,但是让他们欣赏理解,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有好处的。诗能叫人心灵敏感,体察人情。”“对个人安顿自己身心,诗歌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娱乐,如果能喜欢上它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,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幸运的事情。”
中西兼通,文理兼通,天情人情兼通,对于今天的中国学子而言,或许是一个传说。且不论传统文化的异化消解,从高中时代起的文理分科,已经划出了一条鸿沟。
但章诗依并不认为文理分科不合理:“中国现在的高考,就是一门技术,文理分科就是这个目的。考试制度不变,考试方式不变,不分科根本不太可能。但是,从人的角度讲,我对什么有兴趣,对什么有天赋,总会有个分的时候。”
5、民国时代是有很多大师,但追捧民国时代也没意义
在《理工学人的诗与世》中提及的22位学者,都是横跨过晚清、民国和新中国至少两个阶段的人。他们所经历的时代,正逢历史巨变,正是“国家不幸诗人幸,赋到沧桑句便工”的贴切写照。诗人们在书斋里写诗,在旅行中写诗,在野外作业中写诗,在战乱迁徒中写诗,在遭逢不公正对待的年代,也以诗言志。所以,在书中,有个有趣的细节,22位学者中,有11位学者的诗,其选题都与旅途相关,“一个是出国要去求学,要么抗战以后战乱不断迁徙。所以那时候肯定感触很多。”
近些年来,有一个关键词叫“民国热”,具体表现在人们对于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追捧,以及对某些生活想像的浪漫化。但就《理工学人的诗与世》这本书而言,即使那么多杰出的学者巨匠都经历过民国时代,但这并不能成为谁价一个时代的标准。
对于“民国热”,章诗依把它比作一个钟摆。“把它摆到另一边摆得越厉害,反弹到另一个方向的时候力度越大。”当传统认知中,民国被描绘得一团漆黑时,总会有些物极必反的浪漫化想像出现。“大多数人都对自己的时代都不会满意,很少有人欢欣鼓舞地说我生活在一个好时代,都觉得自己所在的时代毛病很多,我觉得这是共性的。就像伍迪·艾伦的电影《午夜巴黎》里描述的,一批人对现实生活很不满意,穿越到19世纪,结果在19世纪的咖啡馆里发现,19世纪的人们正在怀念18世纪呢。”
“所谓最好的乐园就是失去的乐园。”
6、未来的写作计划:仍与历史有关
在章诗依的书房里,除了有着充栋的藏书和影碟之外,还有着他走遍各地采访的留念。但说起重要的收藏,他首选的仍然是书,而且是作者签名的书。其中,有在他任职于香港期间得到的金庸签名书《明窗小札》。“这是金庸先生当时在《明报》自己写的一个专栏合集,这些社评专栏,现在读起来都不过时。”
除了收集理工学人的诗,章诗依还在收集旧时代政要和军人们写的旧体诗。但提到下一步的写作计划,章诗依表示,《大公报》的历史,会是一个写作方向。“历数近现代以来中国优秀的新闻记者,《大公报》里面占了70位。这非常了不起。而且《大公报》里面真的是群星灿烂,各种各样的人才都有。我前不久到浙江嵊州,那里有一个越剧博物馆,发现中国最早的越剧编辑也是《大公报》的记者。这些人后来命运各有各的不同,我很想把他们的命运的悲剧喜剧都挖掘出来。”





